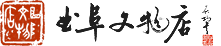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基本陈列厅里,有一件珍宝,因其年代的久远及其雄壮威猛的造型震撼人心,也因此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就是1958年秋天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的细泥黑陶鸮鼎。该鸮鼎高36.0厘米,长38.4厘米,宽30.0厘米。鸮作蹲踞状,体态丰肥,两翼微微撑起,双足壮实有力。鸮头写实,形象逼真,在鸮喙两侧,仅分别各用一刀,就巧妙地将上下喙精确地刻画了出来。作者雕塑能力的高超,由此可见一斑。鸮眼圆凸,炯炯有神,傲视前方,正视之,雄壮威猛之感顿然而生。后足在形态上有别于前二足,扁而宽,显然象征鸮尾,附于鼎腹后方以支撑鼎身。三足内空,壁厚1.3厘米,皆附于鸮腹之下。鼎为圜底,口唇上有子母口凹槽,原来当有器盖,惜已不存。整体观之,体魄雄峻,洗练大气,霸悍凶猛。为一件罕见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塑艺术珍品,当之无愧的国宝重器。
然而,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1958~1959年的考古发掘,到了44年后的2003年,考古报告《华县泉护村》才得以出版。遂使这一并非正式考古发掘所得,而是由太平庄农民殷思义在耕地时捡得(同时捡得的还有一件细泥黑陶小口长颈单耳平底瓶),于1958年秋上交给正在泉护村作考古调查的考古队员的真实历史尘封了几十年,至今鲜为人知。
这件珍宝的出现,引起了考古队的高度重视,便立即派人前往,在殷思义的带领下赶赴出土地点了解情况。在上述两件器物的出土地点,考古队员稍微剥去耕土,便又发现了夹砂红陶灶、陶釜和细泥黑陶钵的残片(釜、钵均可修复,陶灶因过于残碎且陶质酥散难以复原)。因当时正在发掘泉护村遗址,难以抽出人力进一步清理。
同年12月,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组织力量对华县古代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在太平庄上述器物出土的地点,顺着南北方向开掘2×5米探沟一条,未见任何遗物。但在探沟的西壁上,发现了人的脚骨。根据这一线索,顺着脚骨的去向,便发现一座东西向的墓穴。在这里发现人骨一具和随葬的骨笄、骨匕及石斧、石铲等。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这两条探沟内,均未见到文化层,墓葬是直接开掘在生土层中的。1959年一次试掘上述墓葬地点,以寻求墓地。结果也是再未见到任何墓葬,也未发现其他文化遗存。也就是说,这座墓,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孤立的存在。而且,考古界众所周知,泉护村及其四周地区,新石器遗存广泛分布,面积达60万平方米之巨,从那时起至今,却再也没有发现过一座这一时期(泉护一期)的墓葬(1958年冬,在泉护村小学东面,通往元君庙的大路北侧的台地上,仅发现了一座儿童的墓葬。编号为M601)。
1958年12月试掘的这座墓葬,编号M701。是东西向的土坑竖穴墓。由于受自然水土流失或人为耕作等原因的破坏,当时所存墓穴不深,仅30~40厘米。南北墓壁不齐整,两壁中部均向内凹,南北宽60~80厘米。整个墓穴呈头尾大、中间窄的细腰形。墓穴东壁已找不到,当是由于挖掘鸮鼎时被破坏掉了。故墓穴长度不明,残长约2米。如把出土鸮鼎、小口单耳平底瓶、灶、釜、钵等器物的部位估计进去,推测原长当在2.7米左右。
墓穴内未见葬具遗痕。墓内葬一人。据西安医学院人体解剖教研室陈必忠、卢守祥现场鉴定,墓主人是30~40岁的女性。人骨保存较好,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这一点与泾渭流域其他仰韶文化遗址墓葬的主流头向是一致的)。综合上述情况,可肯定属于M701的随葬器物,有骨笄2件,骨匕14件,石斧、石铲各1件。
由于这篇文字是在“藏龙”网上随写随发的,写到这里,看到了网友“恶魔猎手”的这句感慨:“如果,这件重器出现在潘家园地摊上,大家会怎么看,臆造品!”
是啊!别说是出现在潘家园地摊上,就是出现在民间收藏家的手里,甚或出现在民办博物馆里,恐怕也是难免“臆造品”的命运的吧?
后来,我又了解到,还真有一些“国宝”级文物,仅以仰韶文化为例,就有那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鹳鱼石斧图”红陶缸;那件现藏甘肃省历史博物馆的“人头形彩陶瓶”(下图);那件现藏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的“鸟龙”纹彩陶盆……就都不是通过正式考古发掘而进入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啊!
现在有一个问题,中国这几十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非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其数量之大,其精品、孤品之多,是完全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的。但如何对待这些非正式考古发掘文物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近百年的中国考古工作,早已将史前文化的谱系梳理出来了,完全可以用类型学的方法,从共同文化特征的角度,把没有见到过的东西,安放到文化谱系的链条上去。(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李宝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