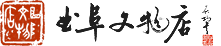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于泰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罘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后言“刻”者,惟于碣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录乎?
在顾炎武之前,有关无字碑的归属只有观点不见论说,自此才有了实际意义上的辩争。顾氏的论据主要有四:一是岳顶已有李斯所篆的秦碑(也就是秦的纪功刻石),不应再立无字碑;二是宋以前无人说无字碑是秦碑;三是《史记》记秦石有“刻”,汉石无“刻”之记,是为秦石有文而汉石无文;四是如果秦皇别立此石,或汉武立石刻文,理应有史记载。自此,无字碑为汉武所为的观点,一直占据着上风。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有人对顾炎武的汉碑论提出了疑问,重申无字碑为秦始皇所立。质疑的立论依据,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从无字碑的高度及形式特点看,属秦制。“从无字碑的高度看,与琅琊刻石相近。石上方有收分,此点也同于琅琊刻石”;“从形制看,碑身削四棱。刘跂记泰山刻石,也削去一棱,‘制曰可’三字,即刻在削棱后的平面上。二者作法相近”。
其二,无字碑的尺寸符合其“水德”的制度。认为无字碑的长短广狭数据合于秦尺的倍数,“可见泰山无字碑的形制符合‘数以六为纪’的制度”。
其三,马第伯《封禅仪记》所说的“石阙”就是无字碑。“此石颇象阙,故其应即马第伯《封禅仪记》中所说的始皇所立阙”。
此外,还出现一种观点:认为泰山无字碑既不是秦始皇所立,也不归属汉武帝,是东汉封禅祭祀的遗物。
这一论点首先以立碑的地点来确定碑的性质。无字碑立于岱顶,“和古代帝王封禅泰山似乎有一定的关系”。二是排除秦始皇、汉武帝有其碑的可能性。论据是:始皇所立石的形式没有时代较早的记载,刘跂所云“四五尺”,与董逌的“八九尺”都未必可信,如与时间相隔一二月所立琅琊立石(引用《山左金石志》材料石高丈五尺),“两石大小似乎不应如此悬殊”,因此刘、董“所见的始皇泰山立石,似乎已经不是原石的全部”;“汉武帝立石被毁的时代可能相当早,见到的人不多,所以对它的形制除了应劭所说的‘高二丈一尺’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记载”。既然秦始皇立石在宋代之时已经不是全石,与无字碑就没有了关系,汉武帝的立石也已早毁,无字碑也就不可能是汉武所立。三是以形制而论无字碑的特点与现存的东汉碑相近,碑身截角的做法,“在西汉至东汉初年的石刻里都见不到”。泰山无字碑制作精致且截角,“只可能在东汉,并且还未必在东汉的初年”。由此结论:泰山无字碑为东汉帝王举行封禅之类大典所留遗物。从到过泰山祭祀的几位帝王看,“泰山没字碑为东汉章帝或安帝所立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假使从碑的形制来看,尤其安帝的可能性更大于章帝”i。也就是说,泰山无字碑应为安帝所为。
有了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安帝三说的论点论据作参考,结合在讨论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我们提出如下基本观点:
第一,泰山封禅的立石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纪功刻石,一个是封石,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以秦始皇封禅为例,在《史记·封禅书》中“立石颂秦始皇帝德”,说的是纪功刻石;“明其得封”,说的是“封藏”之封,是以石为封,是为封石。在《秦始皇本纪》中“立石,封,祠祀”,“立石”为封石,也即封藏之标志石。再说汉武帝封禅,《封禅书》中“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石”之石,应是纪功刻石,“上泰山,亦有封”,此封犹如始皇“封藏”之封,以石为封,此石也就是封石。封石是个标志物,故又有“纪号”之名。关于封禅之仪立石有二,马第伯在《封禅仪记》中就有表述:封禅“治石”二枚,“一纪号石,高丈二尺,广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纪功德”。《封禅仪记》又云“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汉武在其北”,“立石”即封石;“阙”在封石的四面。“汉武帝在其北”,是“汉武帝立石及阙在其北”的省文,“立石”与“阙”是对应的。
第二,封石在封坛,而纪功刻石未必就在封坛。如唐玄宗的封坛在玉皇顶与日观峰之间的太平顶,而纪功刻石在北边的山崖上(现之大观峰,两者有着一定的距离)。宋真宗也是这样,封坛与纪功刻石不在一块。所以说,秦始皇、汉武帝的纪功刻石不一定会在封坛上,不应该一说刻石就到封坛上找。元好问《东游记略》云:“秦观有封禅坛,坛下有秦李斯碑”,“李斯碑”毫无疑问是纪功刻石,表明秦的刻石是在其封坛的下方。
第三,刻石的形制特点具有特殊性。形制往往是判断物体时代特征的重要依据,但就碑刻而言就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封禅刻石更具特殊性而非一般物件所能比。秦始皇是封禅的先行者,本来就没有章法可依,具体到刻石的形式是个未知数,是他首开先例。汉武帝是第一个继始皇而为之的帝王,也曾面临封禅有不知所措的无奈ii,在刻石的问题上对秦制有所借鉴是情理中的事。还有一点也应注意,形制的形成与变化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发展、稳定过程,仅凭一件标本很难谈形制所应具的普遍性意义,更何况封禅刻石又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泰山岱庙现藏有一通明代的《金桥碑》,碑身断面大致呈方形,其高度与无字碑也接近,但两者风马牛不相及,仅从形制做作出判断不可取。还有秦始皇、汉武帝的“立石”,两者时间相距也就百余年,很难作出有价值的区别比较。因此说以碑石的形制来断定无字碑之年代(或秦,或汉),无多大意义。
第四,《史记》所云汉武帝“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所上之“石”,不可能是今之无字碑。在不少有关无字碑的记述中,有“石腻白而坚,非山所产”、“色黄白坚莹,无苔藓,非岳之所有”的说法。其实,无字碑即取自岱顶之石。《岱览》卷八说:“诸志谓石色坚莹非岱产,蒙摩挲久之,窃谓与巅石无异,意就当时石笋划劙而成,以表泰山,故屹屹不可震撼,古称石表者。”据实地考察,无字碑之石来自岱顶的丈人峰。丈人峰岩石高6~7米,在岩峰的一侧现仍有辟石之痕迹;再从其石质、花纹、颜色等看,两者也都是一致的。无字碑位于玉皇顶峰顶的南面,丈人峰在玉皇顶峰顶北面,两地相距190米左右,就地取材省去不少麻烦。测量所得,无字碑碑身高495厘米,碑宽上为112、下为124厘米,侧宽上为69、下宽为93厘米,碑身计有4.7立方米,此花岗岩的比重为2.8左右,以此计算无字碑碑身重约13.26吨。如此之重的庞然大物,依当时的运输手段显然是无法从山下“上石”至泰山之巅的。况且汉武帝是三月令人上石,四月即封泰山,从时间上说也为运输增加了难度。
有了以上几点认识,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泰山无字碑的秦始皇说、西汉武帝说、东汉安帝说。
先说东汉安帝说。此说三个基本理由中的第一点是说无字碑的性质,与争论无涉。第二点是在排除秦始皇、汉武帝的可能性,其论据是秦始皇所立石在宋代已不完整,汉武帝所立石被毁的年代也相当早,由此说明秦始皇、汉武帝与无字碑没有关系是不合情理的。论据的瑕疵在于:一是以刘跂所云“四五尺”与董逌所云的“八九尺”之差异,定论秦刻石已残缺是一个误判,刘与董所言的尺寸差距是因“累石固其趾”造成前后高度不一的结果,与残损无关;二是汉武帝的刻石只因缺乏记载而被认为是早毁也有失公允。退一步说,即便是“残损”成立,也不影响秦始皇汉武帝所立的可能性,因为纪号石与纪功石是两回事,立石有二,是秦汉封禅的惯例。第三点落脚在碑的形制上也缺范例。我们现看到的东汉碑无论是泰山岱庙的汉碑还是孔庙、济宁的汉碑,不见无字碑这种断面呈近似方形的碑体。而其列举的麅孝禹刻石,高不过才1.45米,与无字碑相差太远,况其他方面也多有差距。仅从无字碑打磨“光滑”这一特点,不能足以说明是东汉之物。还有,安帝、章帝来泰山实施的是巡狩之礼,所作所为在《后汉书》有记,不曾言立石、刻石之事。巡狩与封禅在“受命于天”的性质上是相同的,但表现在祭祀形式上两者是截然有别的,立石、刻石为封禅所特有。因此,无字碑不可能是东汉安帝所立。
再看汉武帝说。此说一上来就断定岳顶既已有李斯所篆的秦碑(也就是秦的纪功刻石),“不当又立此大碑”,似嫌武断。如上文所分析过的,封禅立石有“纪号”、“纪功”两石是无可争议的,以有一石而否定另一石的存在实属想当然。其次说宋以前没有人说无字碑是秦碑,但也没人说无字碑是汉代的,反而从明代开始起都说是秦始皇所立,故而此据令人生疑。其三,说《史记》记秦石有“刻”而汉石无“刻”,是为秦石有文而汉石无文,这也是秦始皇说与汉武帝说双方反复争辩,“咬文嚼字”的一个焦点。其实如前文所论,封禅之石刻与不刻是相对而言,如纪功刻石已经刻文字,不必再言“刻”,只有“立”;而如果是封石,那是一个标志石,也就没有“刻”这个环节,只有“立石”。其四,说如秦皇别立此石,或汉武立石刻文,理应有史记载。这又回归到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中,“立石”与“刻文”是两个概念,如果将两者混淆了,在《史记》中也就找不到本来意义的“立石”与“刻石”了。
最后看秦始皇说。此说主要是以无字碑的形制说事,形成它最大的优势。一是从大的方面说无字碑的形式属于秦制,比对的对象是琅琊刻石,这种比较缺少共性。上面我们曾分析,碑刻形制有其特殊性,相互间发生模仿是在所难免的事,况且秦汉时期是碑刻发展的早期阶段,各个方面都还不成熟,秦始皇与汉武帝的封禅时间相距百年,故以此判彼意义不大,何况碑刻形制的形成还有它的局限性,无字碑或秦或汉在形制上不会有迥然的变化。二是由形制(具体的尺寸)延伸到秦以水为德,有“数以六为纪”的制度,即便如此也不能确定无字碑的归属。因为在汉初之时也曾以为汉是承水德之运,因此也无法排除汉武帝以水德之数来营造的可能性。况且,说“数以六为纪”的制度用在了无字碑上也是勉强的,无字碑从整体上看是规整的,但具体到每个面,每个角都不甚规则,其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很难把握(已见发表的数据尺寸几乎都存在差异),仅从最重要的尺寸——无字碑的高度来说,是加之碑盖的通高,还是碑身之高?况且还有碑身嵌入地下岩石的尺寸不明,因此其高度的确定就存在人为的随意性。
此说,还提出了马第伯《封禅仪记》中的“石阙”就是无字碑,也有失本意。《封禅仪记》的“立石”与“阙”,不是一回事,如果说无字碑是“阙”,那就与“立石”无缘,两者是主角与配角的关系。《封禅仪记》云“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汉武在其北”,所言“立石”是纪号封石(其前文有言“一纪号石……名曰立石”),也就是说,在封坛上有不但有“立石”,而且有“阙”。 《封禅仪记》又云:“台上有坛,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维有距石,四面有阙。”“方石”即“立石”,表明在其周围还有“距石”及“阙”分别分布在“四维”与“四面”各个方向。四维(西北、西南、东南、东北方向)有距石;四面(西、南、东、北)有阙,“立石”与“阙”不可等同,前者是主角。
秦始皇、汉武帝、安帝三种说法就观点而论,无字碑为东汉安帝所立可以排除在外。其他两说,如仅从立论到论据来看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过没有脱离《史记》、《封禅仪记》等文献所记,以及岱顶现存遗迹的大致范围,符合秦皇汉武封禅立石的基本条件。可以肯定:无字碑是秦始皇或汉武帝封禅泰山时的遗物。那无字碑是秦,是汉?我们在马第伯的《封禅仪记》中可找到答案,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马第伯说:在东汉光武帝的“封所”可以看到南、北两个封坛,“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汉武在其北”。对这一记述人们肯定不只一次审读过,但却没有与泰山极顶的实际地形地貌结合起来。以马氏所说,在光武帝封坛的南面是秦始皇的立石与阙,在北面是汉武帝的立石与阙,汉光武帝的封坛位于两者的中间。如果对这种说法无疑义,那么无字碑肯定是汉武所为,因为受极顶——玉皇顶的地形所限,如果无字碑是秦始皇的遗物,在其北的东汉“封祀所”,还有再北的汉武封坛,就都没有了着落,因为无字碑距玉皇极顶石的距离很近,在极顶石之南无法容纳下光武帝与汉武帝的两个封坛。是否东汉、西汉的两个封坛在极顶石以北(或悬崖下),也可排除这种可能,因为“祭天于南,就阳位”,所以祭坛不会在其北(阴位)。而东汉元和二年(85年)章帝东巡,“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坛兆”,直接表明汉光帝的封坛在山南之位。因此,受地理形势的制约及礼制规范要求,无字碑只能是汉武帝的“立石”。在此还需补充说明的是,无字碑现有的“碑帽”,应是后人“张冠李戴”的结果。正是有了这种形式的“碑帽”,无字碑“颇像阙”了。
在此再对无字碑的名号作一梳理。无字碑是因其无字而得名,而就其性质而言是“封藏”之石,也是封的标志,故云“纪号石”。明末清初的谈迁在《谈氏笔乘·太山》称:“太山上秦始皇立无字碑,或曰碑函、或曰镇石,或曰表望,或曰待刻。”碑函,是封函之碑(下有石函之说);镇石,可谓高大威然而镇;表望,谓标志以示;待刻,当为无字之义。又有石表、石阙之称,或因形、或谓意各有说辞。但如依无字碑的性质,名其曰“汉武纪号石”、“汉武封石”为宜。
说汉武纪号石,不能遗漏汉武帝的纪功刻石。纪功石自然是有文之石,但其文在《史记》、《汉书》中无载,幸而泰山太守应劭的《风俗通义》有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古有“前汉无碑”之说,宋代陈槱《负暄野录》卷上有文云:
《集古录》并《金石录》所载,自秦碑后,凡称汉碑者悉是后汉,其前汉二百年中并无名碑,但有金石刻铭识数处耳。余尝闻之尤梁溪先生袤云:‘西汉碑自昔好古者回尝旁采博访,要亦非真。非一代不立碑刻,闻是新莽恶称汉德,凡所在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不容略留,至于秦碑,乃更加营护,遂得不毁,故至今尚有存者。
西汉之所以无碑,是因王莽“恶称汉德”、“皆令仆而磨之”的结果。据《后汉书·张纯传》云:“帝乃东巡岱宗,纯从,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可见汉武帝纪功刻石在东汉刘秀封禅之时刻石已经缺失,仅见张纯所献的“刻石文”。汉武帝刻石,有可能就是在王莽的禁令中被毁。
综上所述,无字碑是汉武帝封禅的封坛封石,是泰山封禅的标志之石,也就是即所谓的“纪号碑”。它与“纪功”刻石是两回事,是没有什么文字的。汉武帝之举,或曰傲气,自以为功德盖世不可用语言述之;或曰谦卑,功过要留后人评说;或曰无字碑为几何体“四方无际”(四方无记)之谜底,寓其疆土四方无界,均将汉武帝封禅的“纪号”石与“纪功”石混淆,是为臆说。把无字碑说成是《封禅仪记》中所说“阙”,也有失本相,“立石”与“阙”,在封禅仪注中扮有不同的角色。(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