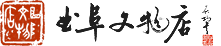我们不止一遍地说过,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文献的记载,文物的流传都是最好的验证。尽管我们的文化历遭掠夺和毁坏,但是大量的文物还是凭借着特有的生命力,顽强保存了下来。说到这些人们可能会着眼于博物馆的珍藏和考古的新发现。其实有些文物甚至很有身价者,就在我们身边悄然而存,只不过藏在深闺无人知罢了,这或许就是天意,难怪人们常常感叹:天遗瑰宝深户藏。
前些日子,到好友兼同事王建忠家里小坐,无意中发现了几方印章。随手拿过来观看,竟然令我大吃一惊:其中一方竟然是清代大师丁敬之作。印文自不必说,密密匝匝的边款,当在七八十字左右。俗话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我不敢以行家称,但是从石章上的包浆便可以看出年代的久远;刀法的老到可以窥见技艺的精湛。我采用人熟不讲理的规则,提出要借这几方印章把玩几天。出于友情,王建忠稍作犹豫竟然答应了。我也无心再山谈海论,包好印章便告辞了。
回到家里,掌灯细看,使我更加惊异不止。丁敬那方刻的是“左右修竹”。经过点数,边款竟然有八十二个字。刻于清乾隆庚午,当是1810年,还特别注明是重阳节的前二日,算来到今天也超过二百年了。印章边缘的磨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于是印文就越发显得突出。典型的风格让人相信,不但是丁大师的真作,而且是精品。尤为让我叹息的还是边款,运刀一似行笔,竟是那般流畅,似见毫端锋芒。而且一气呵成,绝无懈怠之笔,细微之处则更是精妙。观此佳作,即使击案叫绝也不为过。
再看一方“庚寅初度”,一黄色寿山石一面刻印,五面为款,实为难得。此印署名“大羽”,一时难得其详,暂且不问。其精妙处在于四面均有随石形而薄雕的山石树木,在方不盈寸,高略过寸的极为有限的空间里,演绎得那般游刃有余,自然生动,非大匠何能为之?更令人赞叹的是,二十六个隶书文字巧妙补白穿插于图画之间,更是平添情趣,当然含金量也随之而升。那笔法与刀法融合之得当,真是到了极致。加之多年经人有意无意地触磨,石之本性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真是英雄不问出处,我为印章所迷惑,根本不想知道“大羽”是哪路神仙了。
第三方是陈曼生所治的“书痴”,亦是得心应手的精品。想必刻此印时定是心血来潮,换言之,就是捕捉到了灵感,绝非应酬之作。诗书文印皆为一里理,人创作欲望强,作品则神完气足;反之,则疲惫不堪。细观此印,对章法、刀法不必细读各家理论之说。对之书空揣摩,日久自然理解,而且逐步加深。此印可做教材,亦不是空穴来风。
最后一方,署名“漫生”,又是一家所治。刻的是诸葛亮句“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初看,刀法似有艰涩之嫌,看印石便知是青田中的蕉叶石,石质使之然。因石质而表现特有的一种效果,格外以拙见功力,力度毕现。也就是顺其势,展期貌,反之则事倍而功半,枉费气力。此印有一绸布套包之,青面白里,可见主人之珍爱。里子上写有“蕉叶青田”四个小字,当为小楷,略带行意,看得出来非常人所书。
这四方印真且精,今为友人所得,我不为之嫉妒,只是为之欣喜。应该说,这不是四方普通的印章,应该说是文化内涵很深的艺术珍品,堪称瑰宝。最起码石章本身就价值不菲,虽然说不上田黄类的极品,但是经过岁月的打磨,淳朴的实质,自然的纹理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印章出自名家之手,就不是简单的刊刻技术了,而有着对书法、篆刻相关的许多文学素养包含在其间。无论是拓出印模,还是拓出边款,或者是观赏石章都会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我自然是雁过拔毛,请青年篆刻家祝小兵帮忙拓了边款,印了印模,在红、黑、白之间充分地徜徉。 我为瑰宝的传世和有人珍爱而感到欣慰和满足;对于我来说,过目便是缘,便是福。(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崔陟)